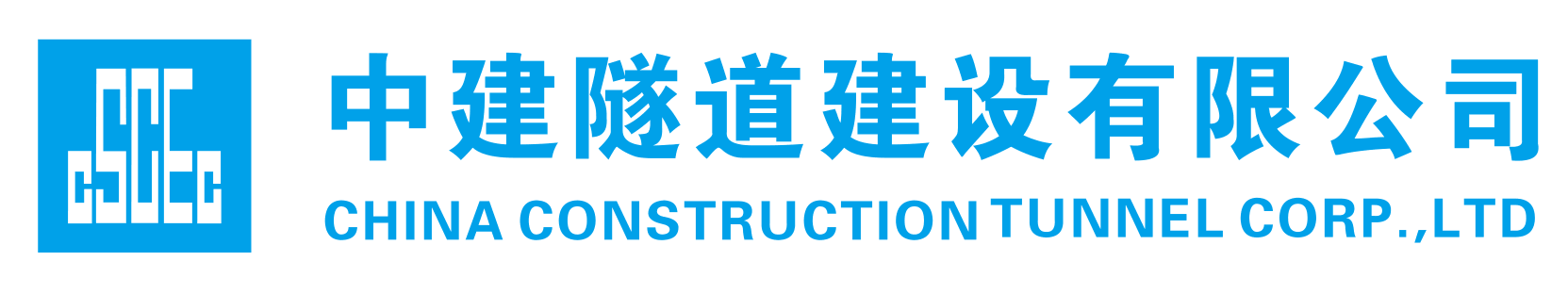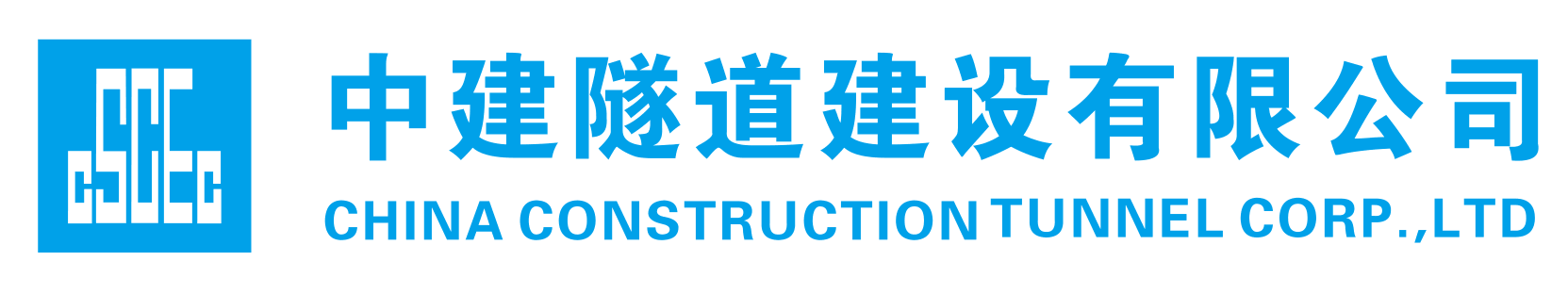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或许只是那浣纱溪边的故乡与童年。
寒月似梦,轻纱如衣;河水涸竭,老竹魅影;碎石缀路,拓了田埂,老了芭蕉……打乱了俗尘五味,混沌不识。
别了前世,故地重游;错了今生,犹在往昔。
那一年,春雨丝润,万木争荣,柳条轻扬,泥土泛香;新燕南归,衔木啄泥,绕屋盘旋;阳光暖人,微风如醉,万里芬芳;我爱放着风筝,我爱跑着,我爱追着,因为我想看看更辽阔的远方。
那一年,雷电四起,风急雨骤,折了树枝,没了河溪;白鹭低飞,青苗低垂,房盖上噼里啪啦,檐下水如长线。我目不转睛,等待着云开雨霁,虹桥初现;那一年,星夜浩瀚,繁星如缀,我穿着小布衫,平躺在地坝凉板上,枕在奶奶的怀里,边上奶奶的蒲扇轻摇着,我深黑的眸子入迷的仰望着星空:“哪个是北斗七星,哪个是天马座,哪个是射手座?”又觉银河璀璨,我怯生了渺不可及的感觉,忽又凉风习习,不知何时闭上了眼,这一梦,好似过了千秋。
那一年,蛙声一片,萤火点点,稻田里蚂蚱漫天飞舞,谷草碎枝迎着几分燥热飘落,金黄的稻粒满载箩筐,一年丰收的喜悦不分昼夜;那一年,红柿枝头,我们三五成群,踮起脚尖,搭着人梯,摘得满兜;那一年,深秋浸来,凉意渐生,枫叶似火,傲然于林。我拿着铅笔计算着应用题,蚊蝇叮咛,惹得我心不从一,我抬头便看见了一抹艳丽的晚霞沉浸西山。
那一年,稠雾笼罩,晨光熹微,草垛子上寒霜凝结,水面上薄冰渐现,我拿勺子小心的舀上一块,如获珍宝一般,只见浮波荡去,便是一个冬天……
那一年,小河悠悠,流水潺潺,几块青石躺在细水间,清风侧起,翠竹摇曳,斑驳的竹影载着滑落的竹叶畅游;落日余晖,只闻妇女们挽着长袖,打着清幽的拍子,浣着溪纱。
那一年,骄阳似火,碧天丽地,小坡上种植着漫山的小麦,夏风微漾,麦海悠悠,年迈的松树卸去华丽的衣裳,几枝新芽慵懒的沐浴着阳光。我们奔跑在田间小路,额前汗粒晶莹,为了尽快赶到学校,丝毫不觉疲累。偶尔的好奇便是摘下麦田里的燕麦,细细弄作一翻,就可以发出悦耳的空鸣。空旷四静的田野,暖风拂面,衣袂飘飘,一曲长笛,随风入梦,吹奏着夏日的幻想……
那一年,我养过一只狗,因头大脸圆而起名“汤圆”,每当放学回家,离家即便还很远,它就耷拉着耳朵,摇着尾巴,满是欢喜的向我扑来。夏天热了,电风扇卖力地摇晃着,我躺在床上睡着午觉,它就和我一起吹着风;冬天冷了,我盖着两床被子,它也在床上睡着。早上起床,我总是大叫道:“妈妈,‘汤圆’又跑到床上来了!”
那一年,少年好武成痴,剑眉星目,白衣胜雪,傲然正气,立志成为江湖侠客,斩尽世间的恶,于是削竹为剑、裹布成鞘;苦练拳脚剑招,飞檐走壁,到头来,只是空了一季烟雨。
那一年,羸弱的身影背着厚重的书包,远方来往的汽车喇叭声划破长空,夕阳的余晖洒在青石的路上,灰尘铺就的公路一望无际,仿佛看见了星月冉冉升起,又或是黎明到来的刹那光明。只觉那一刻,便是永恒。
那一年,稚嫩的面容,青涩的微笑,简单的马尾,毫无顾忌的嬉闹,在记忆的长廊久久萦绕……
……
我常在回忆,却只有些零碎的片段;我爱这片土地,却总是显得不知所措。
我用二十三年的生命来守护,守护那田、守护那地、守护那溪、守护那人,最终却只换来了暮霭沉沉的空寂。
儿时的玩伴早已各奔东西,就连得过年的短暂相聚也成了一种奢侈,莫名想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知四十年后,我们是否白首迟暮,口齿模糊,又是否能够想起我们曾在这一片故土欢笑?
或许当城市华灯升起,歌舞升平时,那躲在角落的故乡,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村庄,正在黑暗中迷茫……
我似乎再不能仔细感受到你四季的变化,不能再感受到那平常人家浣溪纱的欢笑,是我们的五感变得麻木?亦或是我们选择了麻木?毕竟我们都在被忙禄着……
我盼望着,盼望着油菜花开,君自归来!(文/龙洲湾隧道工程三分部: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