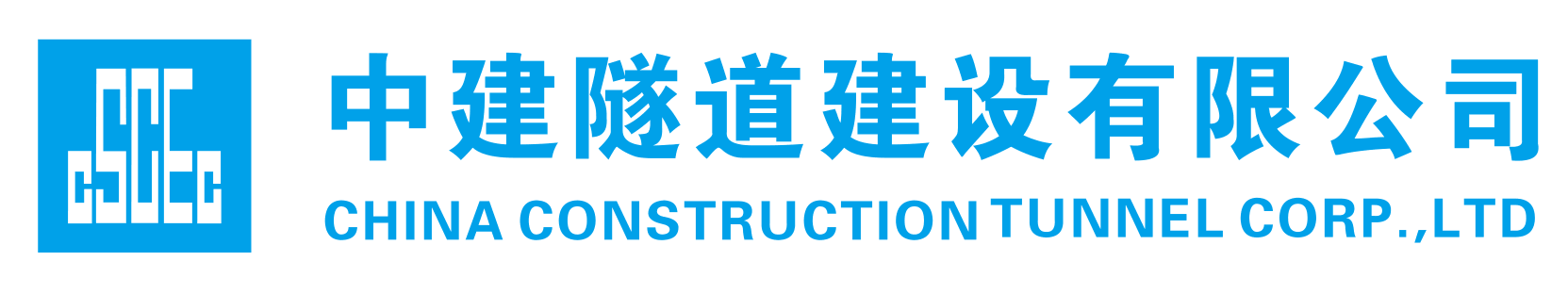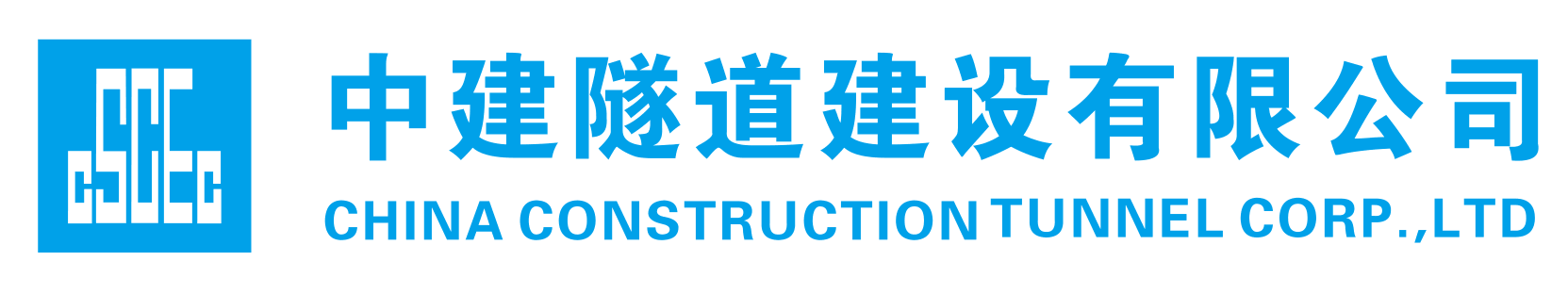不知从何时起,故乡的春,便逐渐褪变为记忆中开始泛黄的早年影像了,许久未见,久得让关乎这个季节的回忆都伴随着幼年的身影,稍近点的人生竟似乎于此无任何交集。在这个季节曾频繁接触而现已不多见的部分老物什,在脑海中得用家乡话斟酿好几番,才能略显生疏地组合出那些已不常用的方言词汇。 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大致说的是,一个盲人在行乞,身前挂着纸板写道,“从小失明,乞讨为生”,然而罐子里却空空如也。这时,一个诗人经过正好目睹此景,在牌上重新写道,“春天来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到”。当诗人再次路过时,乞讨者已收获丰厚。让行人唤起同情心的,正是春的美好。初次读到这个故事,当时内心里几乎毫无波澜。也许是映衬了这句话,“在繁华当中时间过得很快,你一旦对时间有感觉,大概就是繁华已经过去了”。现在,春季在整本日历中仍占据着四分之一的厚度,而与那段年华渐行渐远的自己,只能回味着“惊蛰”、“谷雨”等节气内涵而陷入过去的回忆中。 记忆里,春季总该是这般模样。温暖湿润的空气中,随处弥漫着新翻的泥土清香,伴随着万物复苏的气息,使人置身其中而觉身心舒畅。沐浴春风过后,成千上万朵紫云英似一段段锦缎装点着大地,尽情绽放后,在耕犁下“碾作尘”,融入春的泥土里,孕育着又一片绿的生机。在春日暖阳中,农民们戴着草帽,挽起裤脚,弯着背,用手插着秧,以四周阡陌为框,在农田这块画布上挥洒着他们的创造力。 记得上学途中,会经过一段两侧开满刺槐花的石子路,开学第一天,有个小孩总会背着沉甸甸的书包经过这里,有时候他会在家里拿来一个大纸盒,将够得着的刺槐花摘下并拿回房间里,他知道,盒子里的白色小精灵将香溢满整间屋子。而明明可以将新发书本放在学校课桌里,他偏要固执地全部背回,因为他内心有着这样一个小秘密。有个名字里同样带“槐”的老人家总会满心欢喜地等着他归来,他会戴着眼镜,用布满皱纹的双手折着旧报纸给这些教材细心地一本本包着书皮。书中飘散出的淡淡油墨香,老人包书皮时幸福的眼神,暖阳里洋溢着微笑的侧脸,是那个季节最温馨的画面。 回家的最后两百米路,春天里,两侧的农田总会开满成片的油菜花,老人家漫步在这片金黄的花海中,手提着一个用书本折成的纸灯笼,逢人便夸赞道,“瞧!这是我孙儿折的!”。他总是拄着一根竹杖,快到家时,竹杖落在水泥地上会发出“哒、哒、哒”的清脆响声。老人家前后总跟着两只欢快的狗儿,它们总是提前在高处眺望着那个特定的方向,发现那再熟悉不过的身影,立即拔腿奔入油菜花海中迎接老人回家,并在腿边相互嬉闹着,竹杖声与狗儿奔跑后的喘气声交织着,那便是亲人到家的讯号。 如今,于故乡,却已然是匆匆过客,金黄的油菜花海,香气袭人的刺槐花径,生气盎然的紫云英田,却成为了唤醒故乡春季记忆的几个符号。总翘首企盼并在花海中奔跑着迎接亲人归来的狗儿们只留下了十多年前在未干的水泥地上踩下的几朵梅花;老屋东南方的田角上,老人也如同春季里的紫云英永远地融进了这片见证了一生的乡土中。(文/中建隧道盾构分公司长沙地铁5号线项目部:陆彦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