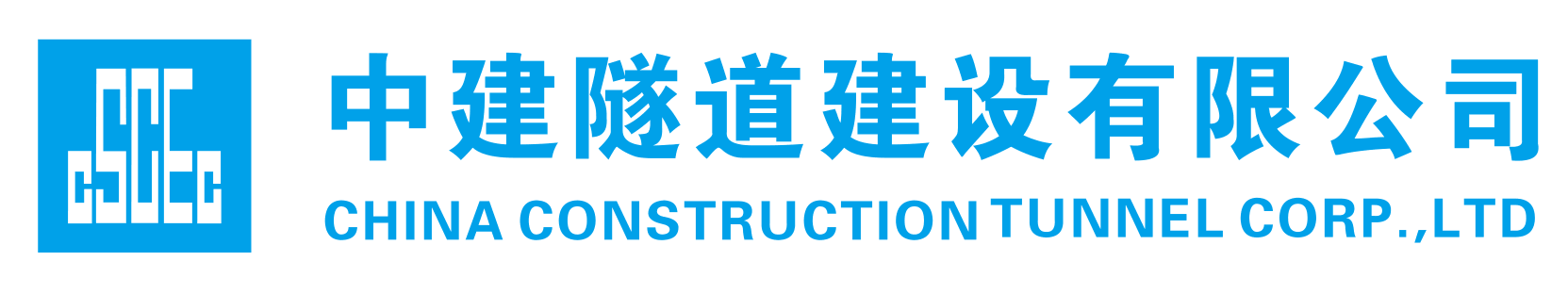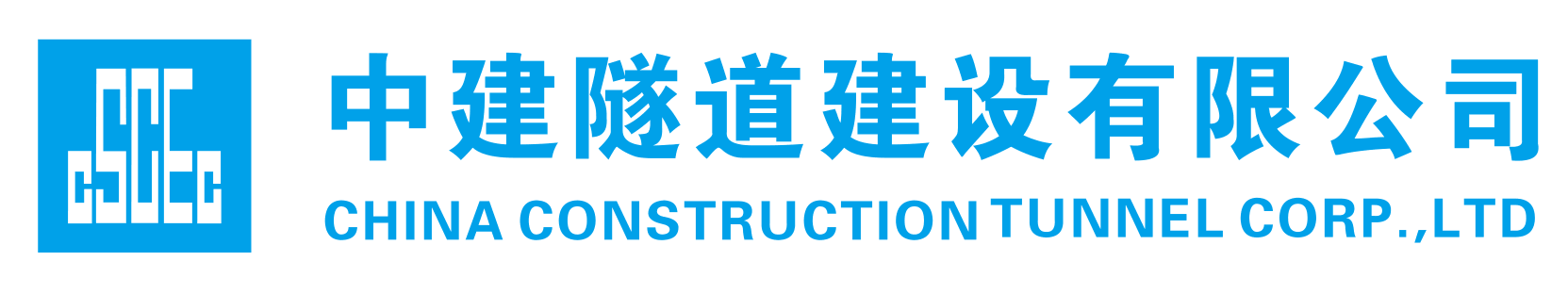不觉间,已经二月二了,虽说故乡在这一天并没有剪“龙头”的习俗,但童年里一些有关理发的回忆却在此刻涌上心头。 老家位于南方某不知名的小乡村,那时,只有镇上唯一一条相对繁华的街道设有零零星星的几处理发店,居于乡镇一隅,在摩托车尚未开始普及的年代,距离“经济中心”略远的人们,大多时候选择的,其实是另一个正在被时代遗忘的群体。 农村的普通平房里,一个正对着道路的房间,一个挂着不同用途毛巾的脸盆架,一把发出嘎吱嘎吱声、有靠背的高凳子,一张摆放着肥皂盒、剃头刀等用具的桌子,一面镶着旧木框表面泛黄、斜靠在斑驳墙面的镜子,一块沾着岁月印记满是污渍的围布。便是乡村理发师的标准配置。乡村理发师大多是有着几十年剃头经验的手艺人,没有时尚酷炫的门店招牌,没有宽敞明亮的理发环境,没有舒缓优美的外放音乐,靠的是从事几十年的“毫末技艺”与“顶上功夫”。虽说是理发师,其实,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这一行业。在春耕的日子里,他们也是农民,也会插完秧提着解放鞋回家,裤脚挽至膝盖,小腿上裹满泥巴。 那时候,奶奶总是领着不情愿的我,走过一段又一段田埂,前往那个在一大片荷塘边上的“剃头点”。理发的是一位老人家,剃头点正是他的住处,费用比较便宜,一次仅收一元钱。记得理发的那间屋子很小,而且门窗朝北,加之灯泡亮度不够,房间整体比较阴暗。老人家年事较高,视力有所下降,但剪起头来,仍颇有一股久经沙场、宝刀未老的气势。在那个没有电吹风的时代,头发清洗完毕后还残留的头发茬子,老人家会一口一口地细心给你吹净,那时候,被吹了一脸口水的脸庞却也是一种幸福。光阴似箭,剃头刀下的孩童逐步成长为爱美之心渐长的少年,而岁月不饶人,老人家刀下的作品却没有那么完美了。随着时光将这种人生代谢的落差逐渐拉大,经受过几次嘲笑后,不知道何时起,奶奶再也拉不动固执的孙儿穿过田野去乡村理发师处剪头发了,而那个理发的老人家也逐渐变成记忆里慢慢褪去的早年印象了,只是后来似乎无意间听说他终于拿不了剃头刀了。 乡村理发师,在时代的洗礼中,终将无奈地归于沉寂。后来,也懂得了,奶奶坚持数年带着孙儿去乡村“剃头匠”处理发,远不是为了那低于物价水准的一元钱费用。那些年,她在理发这件事情上还能为晚辈们付出,她没法骑车带孙儿前往镇上,她只是满心希望将这件当时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坚持得更久些,再久点。她深谙这一现实且无奈地接受着,时光无情,时代会湮没乡村理发师这一行业,也会慢慢地让那些她心甘情愿付出却终感无能为力的“力所能及”成为渐行渐远的过去。(文/中建隧道长沙地铁5号线项目:陆彦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