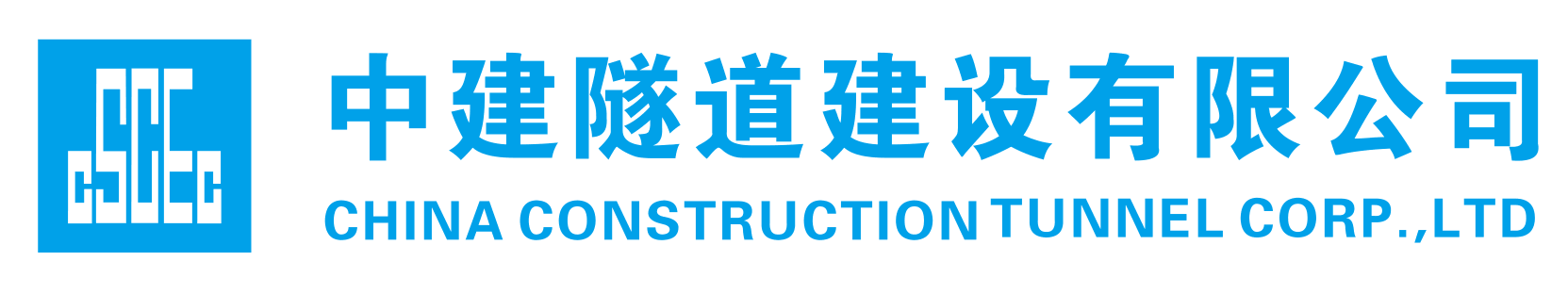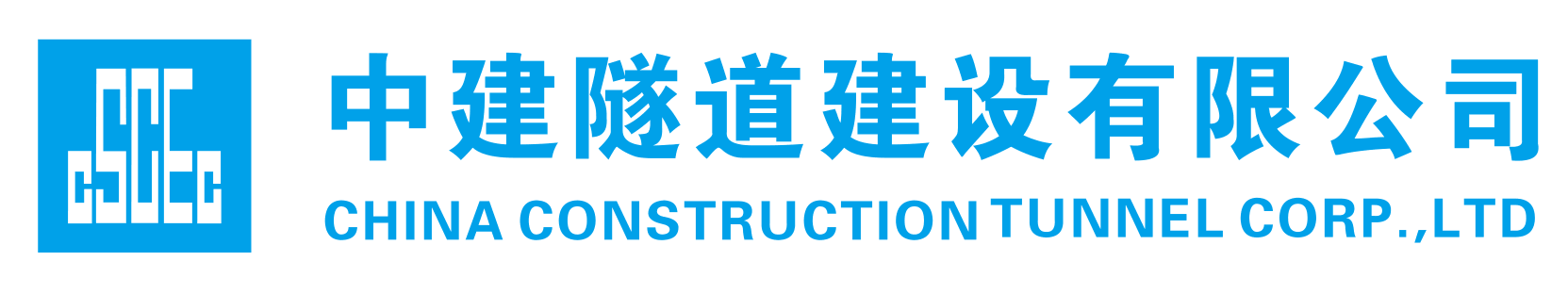我想,母亲应该是一只野鹤,慈爱、孤独而充满痛苦和忧伤。 那只是鄂西南山区一座普通的吊脚楼,空旷、古幽,濡染着土家人特有的宁静和安详。就是在这座吊脚楼上,母亲匆匆卸下盛满猪草的背篓,产下一个男婴,那就是我了。刚出生的我仅有四斤半,像刚孵出的小鹤一样柔弱。 那段时间奶奶逢人便说:哎呀,这不足月的孩子怕是过不了这个年了,她把我不足月便出世归罪给母亲。一如既往的,母亲默默地接受了来自家人乃至四面八方的白眼,细心地用绵薄的乳汁喂我,可贪嘴的我就是吃不够啊,于是,她就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到冰冷的灶膛给我熬米粥喝。就是那甘甜的乳汁和米粥,让一个弱小的生命熬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母亲却落下一身病痛。许多年后,每每看到她因疼痛而扭曲的面孔时,我的心就会一下紧过一下的抽搐,那是一种母子连心的疼痛。我无法回避无法躲闪,是因为母亲为我受的所有苦所有的累,还有她爱我的点点滴滴,都在某个刹那汇成洪流,将我席卷、包围,让我痛哭流涕。我一直都相信:那一只野鹤在寒冬腊月里用自己的血喂养小鹤的图景,就是这人世间最凄凉的美丽。 柔弱的小鹤一天天长大着,强壮着。母亲感觉到小鹤正慢慢长出思想,而她知道:一旦长出了思想,小鹤就会永远被逐出人性的乐园,因为这个个世界不光时只有鲜花和蝴蝶,还有毒蛇、丑恶,更有歧视、污蔑。她实在不想让小鹤的一生荒芜在这块无知而落后的土地上。于是,一背篓一背篓的土豆,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换来了纸和笔,换来了崭新的书包。就在某一天,我扔掉了手中的牛绳,洗净了腿上的污泥,走进了明朗的校园。明亮的玻璃,整齐的书桌,散着油墨香的新书,让我有三分眩晕,却又七分兴奋。也许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从此以后,飞翔的小鹤越去越远,越飞越高,吊脚楼的空旷古幽、母亲的繁忙劳作都一齐被时间和空间抽象成很小很小的一个圆点,在我那张被填的满满的课表中,偶尔被瞅见,却在很多时候——被遗忘。 2004年的秋天,当校园中那颗梧桐的最后一片黄叶飘落时,我的教室外来了位不速之客,是吊脚楼隔壁的三伯娘。她一看见我就气喘吁吁的说:“娃,坏了,你妈住院了!”我不知道自己时怎么走出教室的,又是怎么样坐上回乡的公车的。当我颠簸100多里路到达乡卫生所时,天色已近黄昏。我轻轻推开房门,看见母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一张瘦得剩下皮和骨的脸慈祥的沉睡。这就是我那精力过人,日夜劳作的母亲吗?这就是我那在电话里说自己身子硬朗可以一顿吃下三大碗饭的母亲吗?我的眼泪我的羞耻我的愧疚我的自责一齐涌了上来。但我不敢大声哭出来,怕惊醒了沉睡的母亲后见我哭她自己也忍不住一起哭泣;怕那疼爱我的母亲顾不得自己心脏如刀绞般地疼痛来替我拭去眼角的泪水。我蹲在墙角,捂着嘴,感觉得夕阳的余晖好刺眼好刺眼,刺得我都睁不开眼睛,刺得我眼里充满了热热的、咸咸的泪水。 母亲只住了三天院,就坚持说自己已经好了,不用再花钱住院了,还叫我无论如何要回学校,快高考了,学习耽误不得。家人都十分清楚母亲在想什么,严重的心脏病已经慢慢吞噬了她曾经健壮的身体,病入膏肓的母亲害怕在她身上多花一分钱,说自己用钱还不如把钱用在娃身上有用。精打细算的她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里,时刻都割舍不下的还是她的小儿子——那曾经用母乳和血喂养的小鹤。她让我专心念书,不要挂念她。可母亲啊,你可知道,我的血管里,始终都是奔流着您的血液呵!您疼痛,儿也会疼痛的啊!最终母亲还是回到了那座古幽的吊脚楼,她说她喜欢吊脚楼,那里冬天特别暖和,她怕冷,她要在吊脚楼里等着春天的到来,她说只要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自己的病也就好了…… 也许,18岁的我还太年轻,太幼稚,还不习惯更无法接受离别和死亡。我所能做的只是默默祈祷。2004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还是悄然来临了,它素裹了古幽的吊脚楼。母亲的意识也在这一天模糊起来:她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快跑,坏人来了。然后又自言自语,路好黑啊!我惊恐地紧紧抱着她,喊着她,想唤回她的意识。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母亲就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再也不能燃烧片刻了。她的眼神变得泛散,神采慢慢消失。苍白一点一点吞噬她的灵气,寒风一点一点带走她的体温;那喂我米粥的双手不再灵活,那哺养我的乳房不再丰满……尽管之前我曾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幕,我以为我会坚强。可此时,一只小鹤——一个儿子撕心裂肺地喊出了:“妈——!” 漫天的雪花还在肆无忌惮地飞舞着。跌落山谷的野鹤体热尚温,香魂已逝;身边只剩下嗷嗷待哺的小鹤在雪地里匍匐挣扎,凄凄哀嚎!这只小鹤或许还不知道,它已经成为心灵意义上的孤儿。母亲啊,你不是说要看到春暖花开吗?你不是说要看小鹤飞得更高更远吗?你哺时说还要抱孙子吗?当我说今年冬天会用自己从生活费中攒出的钱给你买毛衣时,你还责备我尽想些无用的事;你不是还答应我将来能赚钱了,要我给你买好多暖和且漂亮的衣服吗?可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 2004年冬天的第一场寒风,送来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带走了我那慈祥而苦难的母亲。 不管怎么样,时光还是拖着我滑过了那么悠长的一段人生。于是我再也无法找到以前的我,那个4斤半的我,那个躺在母亲怀里喝粥的我,那个无忧无虑站在吊脚楼数星星的我。一切都走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是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难道步入成年,非得要经历这样狰狞而痛苦的仪式么? 野鹤跌落,母亲像一个谜一样被掩上厚厚的黄土,在冷清的山岗,任人遗忘,任荒草漫湮;飞鸟归来,在遥远的雪野冰城我筑巢定居。在这座喧嚣都市的某个角落,隐藏了太多关于鹤的泪水。我该拿什么祭奠您呢?那可敬的野鹤,我慈祥的母亲?在两千五百公里之外那座繁华却日渐平庸的冰城里,飞翔的小鹤失去了智慧,失去了荣耀,只有将不肯消沉的灵魂摆上祭坛。 ——仅以此文献给天下母亲 (文/中建隧道长沙地铁4号线六项目:谢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