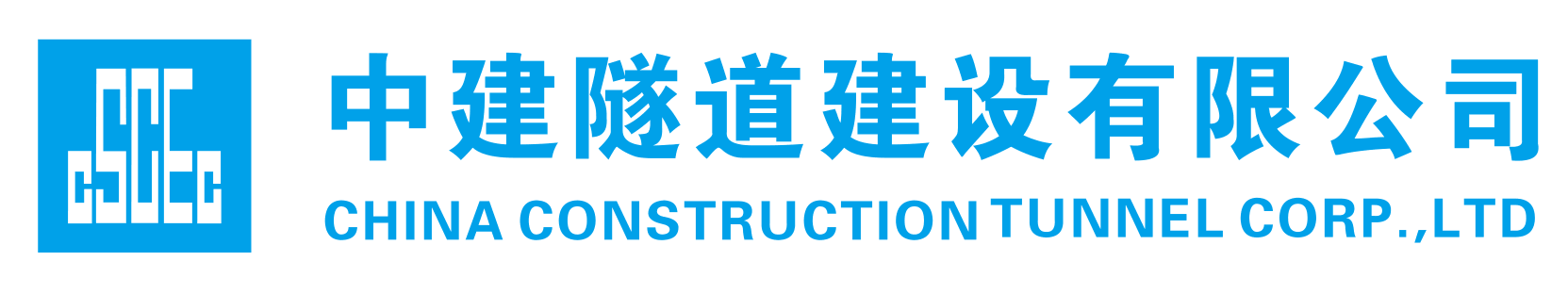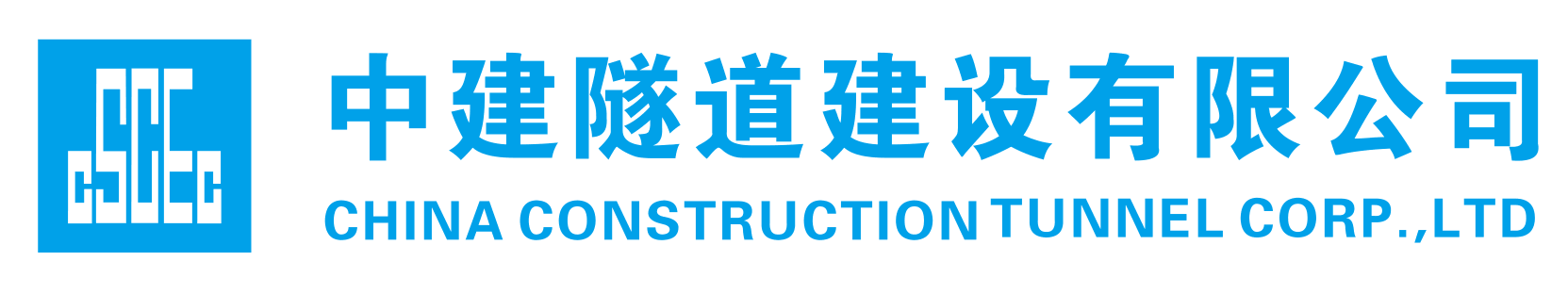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这些词语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如陨石般地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战栗,甚至荡漾出几度酸楚。而当我想起辞世的外公,竟让我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被词语压迫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外公出身行伍,后来弃军从政,从武装部长调任纪委书记,一身刚正清贫,退休后仍摆摊卖农药过了些许年。但唯独对我有些许溺爱,会时常捧着我挨了戒尺的手摩挲良久,会时常买些玩具和塞一些零花钱给我,当然也会因为我考满分而满脸笑意。儿时的片段记忆模糊,外公和我在一起的情景却一晃如昨,温情流淌遍全身,陪着我成长,离别…… 在2015年,我似乎才真正认识到死亡。那时候我20岁,一向身体硬朗的外公在一个星期之内便与世长辞。在我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犹如抽干血液的一具躯壳,瘫坐地上久久无法释怀。母亲亦在我面前始终崩着那根已然断裂的弦,绝不肯掉下一滴眼泪,却在夜间时常哽咽哭泣。回想外公对母亲的宠爱是旁人无法比拟的,家里的房子装修,都是外公一人操持,我去外地的求学之路,也是外公送了又接,来回安排。可终究世事无常,最疼爱的人突然撒手,竟让母亲泪满衣襟。如今窗外马路灯火辉映,犹记得母亲带着哭腔说:“街上那么热闹,却再也见不到我的老父亲了。” 外公和外婆的日常虽算不上什么爱情佳话,但也是彼此恩爱,相互扶持。外公在部队那会儿,外婆便时常做一些土豆饼,搭好几天的车给外公送去,路途颠簸,晕车的外婆呕吐的时候仍不忘紧紧握着那爱意的行囊。外公亦体谅和心疼外婆,工作所得一并上缴,为博一乐。外公的走,最悲的定是外婆了,当时因家乡风俗,外公逝世一星期后,棺材仍在老家村庄的灵棚里放着。一日清晨,母亲给外婆打电话,外婆说她在回村的路上,母亲不解,询问缘由,外婆说,我昨晚梦见你爸还活着,我想回去看看,听听棺材里是否有响动……在后来此事一直是我心里不愿提及的,每一次的想起便让我心颤许久。今天敲出的这话语,红了数次眼眶。外公当时离世已经七天有余,是怎样的思念至极才能如此。 野夫的《乡关何处》是柴静做的序,其中提到,野夫写文章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的气力已经用尽。初读此时,背上竟陡然生出一股寒气,迅速浸满全身,发颤的同时更多的是共鸣。外公的事是我一生难掩的痛,去年题目早已拟好,其中数次提笔,均悲痛难忍停笔,有时洋洒写了几段,早已呼吸难促,蜷缩在床良久才能平复,删了又写,写了又删,外公生前和住院的诸多往事,仍是我不敢触碰和无以言表的,害怕心里结痂的疤如决堤洪水再度溃烂难医。 如今岁月悠长,而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是我一直不敢苟同的,逝者已矣,我知再也无法与他们相见,但他们给我的影响还在,感情还在,他们仍是我人生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或许某一刻我们泪如雨下,我们泣不成声,但我惟愿逝者永存,生者安然,不管何时何地,物非事迁,你们依然是我最心疼的人。(文/重庆分公司重庆轨道九号线11标:刘文吉)
|